林绍灵笔下的“江南”,不是花花绿绿,不是一味的水墨氤氲,而是从那些老房子里仿佛看到操劳的大妈,听到朗朗的书声,体味到历史的纵深感。
“来自地方的画家”
在一次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举办的“中国著名中青年水彩画家十人展”上,主办方在介绍参展画家时,名字前均带个前缀:“来自某某艺术院校”,说明很有来头,唯独介绍到林绍灵时说:“这是一位来自地方的画家。”听了这话,林绍灵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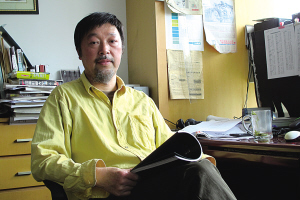
是的,他来自地方,来自江南水乡宁波,没有进过高等艺术院校。因为喜欢,靠自学,在中国画坛赢得了一席之地,曾三获中国水彩画展大奖,这在“地方”是不多见的。
林绍灵1957年出生在宁波西门口的一幢老房子里,小时候的家枕河而建,开窗见水。若从高处俯视,老房子黑压压的一片,偶尔能见到缝隙处,除了不宽的街道,便是河流。林家祖上是大户人家,现海曙区文保单位——林宅的主人便是林绍灵祖上的家族成员。少时,他常和伙伴们到河里去钓鱼,到乡下的外公家去逮蛐蛐。童年水乡的记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那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宽裕,一位看相的先生曾对他父母说:“这孩子将来的生活只能是靠自己了。”
在效实中学读初中时,一次课堂上,他偷画老师徐东明,结果被调皮的同学抢过去上交。徐老师看了看,对他说:“你喜欢画画?我也喜欢,但我画得比你好。”第二天,徐老师拿来自己的水粉画《沙家浜》中郭建光剧照给他看。上课不听讲,还偷画老师,不但没受批评,还得到老师的鼓励,他打内心敬佩起徐老师来。
语文课上,冯老师将一张鲁迅像事先拿给林绍灵看,让他画一张大的。上课铃声响过,冯老师夹着他画的鲁迅像走进教室,慢慢地展开,钉在黑板边上,开始讲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自信,有点像禾苗,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才可顺利成长。若被风霜侵蚀,便会一蹶不振。从小不善交际的林绍灵在孤独的世界里,似乎找到了属于他的自信,绘画的兴趣更加浓厚,并担任起效实中学学生美术组组长。
也是在中学时,一位老师借给他一本厚厚的前苏联《星火》杂志合订的油画册页,他看着起劲,照猫画虎地临摹,与一帮画画青年画写生、练速写,几近痴迷。由于性格喜静,他不愿意过多地跟人接触,更多的时候,习惯于自己静静地观察事物。
高中毕业后,正赶上“文革”后期,未能分配工作,他被安排到宁波七中做美术代课教师,林绍灵真正的美术创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那年他21岁,看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他也创作了一幅油画《班主任》,画作在市里获得二等奖。这对一个自学中的青年来讲,是莫大的鼓舞,从此他成为市里美术创作的一员。后来他被分配到印刷厂从事设计,1984年报社招美编,他走进新闻美术队伍。

林绍灵画作《风雨同舟》
“突破是我的一贯追求”
水彩画的颜料是透明的,讲究表现技法,追求光影效果,在西方多以肖像、静物、风景等清新明快的小幅作品出现,在欧洲贵族中很是流行。被引进国内也有上百年历史,这种表现小情调的画种,在“文革”中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情调,遭到批判,画水彩的人失去了阵地,从业人员越来越少,这门艺术在国内几近灭绝。
“文革”刚结束,中国美院(当时叫浙江美院)的老先生们便成立起水彩、水粉画研究会,林绍灵便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技法,了解行业动态。1989年,中国美院在全国率先举办水彩画大展。随后,中国美协也搞全国性的水彩画展。他每次都参展,并感到水彩画有着其他画种不可替代的意境与美感,也能从其他画家身上学到新的技法。他拼命地画,街景、人物、风光,挑自己满意的,拿到全国去展出。
从小时候画国画,后来画油画、水粉,到迷上水彩,林绍灵走过一段艰难的探索过程,之所以把自己定格在水彩上,他觉得这个轻便灵活、讲究技法的画种,更加符合自己,更有利于内心那种欲望的表达。他说:“当水彩画成为我表达审美情趣的艺术载体时,我既希冀沉湎其中,又能融汇各门艺术之所长,并全身心投入其间而乐此不疲。”
上世纪90年代,他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特别是在人物画创作上,他以人物表情系列、藏民、敦煌人物、兵马俑等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画作,受到国内美术界的重视。
1995年,全国首届水彩画邀请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开幕式上,著名画家古元先生一幅幅地看过来,看到林绍灵的画作《装车》时,停下脚步,认真地观看许久,问他:“你这毛驴怎么画的?简直画活了。”林绍灵马上给老先生讲解,两人还愉快地在现场合影。古元先生不仅版画出名,同时也是水彩画大家。让古元先生感兴趣的是林绍灵对画作水份的控制,画面中的小毛驴显得惟妙惟肖。
水彩画《走向光明》,表现一群青年矿工出井的场面,人物显得放松和自信,画面采用摄影聚焦式的处理方法,将多人场面处理成虚实结合的效果,在技法上采取多次重合湿画法,把水色的渗化和叠加,巧妙地运用到一起,表现了不同光影的区划和笔触的意趣,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主任黄铁山评价说:“林绍灵聚焦式的对画面的虚实处理为多人场景描写提供了新的方法;他在运用水色过程中对色彩、水份、时间三者的成功把握和对于干、湿画法的结合运用又提供了水彩画技法的新经验。”1996年,《走向光明》参加第三届全国水彩画、粉画展览,获得金奖。
有趣的是,当初在创作主体人物时,画家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形象,苦思冥想,难理头绪,创作进入焦灼状态。猛然间,他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这样子不就是自己要表现的强壮矿工吗?他描摹下镜中的“他”,如此,自己就成了这幅获得金奖画作的主体形象。
生活中的林绍灵仪表堂堂,浓眉大眼,一米八的身高,走起路来步子稳健,铿锵有力。过知天命之年后,他蓄起了胡须,更显得老成持重。
自此以后,行进中的人群成为林绍灵大场面人物创作的一个主线,也成为林绍灵在水彩画界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一个特定标志。从人影模糊的“新人奖”《走进阳光》,到中国百年水彩画展的《行色匆匆》,人群走动时形成的虚实,被他表达得淋漓尽致。直至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上的《步履》,风格演化为去年参加全国第九届水彩画展并获“中国美术奖提名”的《风雨兼程》,林绍灵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行进中人群的主题演进与形式风格突破。
“我的画一直都在寻求突破,我不愿重复自己。探索始终是我追求的一个命题。”林绍灵说。

林绍灵画作《逝去的风景·江南》
心中的“江南”,笔下的“江南”
严格地说,林绍灵有两个“江南”:一个在心中,一个在笔下。
他从小生长在水乡,心灵中最深的烙印便是江南的影像:老木屋、小河、石拱桥、破旧的木船,还有那斑斑点点的白粉墙,这些景象伴随着他度过整个童年时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切都在改变,有的像是瞬间的事。他心中的“江南”开始变得混沌起来,他感觉到了模糊,触摸到了流逝,他要把那些记忆留住。于是,他开始真正审视江南,用心画江南,在多年水彩画创作的基础上,从写实,不由自主地进入到“写意”状态,便有了《逝去的风景·江南》系列画。
他的画,不像有些画家画江南那样,表现规整的房屋、洁白的马头墙、清晰的小桥流水人家、鱼鹰悠闲,而是更多的体现江南文化的意象。
画面中房舍是错落的,老石桥是残破的,河埠是半损的,粉墙是斑驳的,脑海中的“江南”,一点点地、真切地出现在画纸上。
每每谈起这些,都令他感慨:“江南一直是我魂牵梦绕渴望表达的景观。今天,我在水色的浸渍中,情感深处的心象突然跃于纸上,有些朦胧,有些暧昧,却带着意外与惊喜,画面中淹没了的轮廓竟由此显得绰约多姿而意味深长。”
他把创作《逝去的风景·江南》时的状态称作:得意忘形。他说:“当我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便会用笔急起直追心底涌动的景象,情不自禁地挥写。”
于是,他不停地穿梭于江浙、皖南等山野乡村,有时一去就是几天,一个很狭小的视角便足以吸引他半天坐下来写生。他说:“这些老房子我再熟悉不过了,哪里该开窗子,一年四季住里面的感觉会怎样,我都清清楚楚。”前不久,浙师大组织一次写生活动,林绍灵应邀参加,一位中国美院副院长看了他的写生稿后对大家说:“画得多充实,你把村里的场景画得如此厚重……”正在进行报道的浙江卫视报道组,竟特别为林绍灵拍摄了关于写生与江南创作的专题,在卫视节目中播出。
去年,他应邀到奥地利进行为时3个月的写生,其间在中法友好协会的协调下,在法国波尔多市做一个展览。古老的画廊就处在市政府旁,画廊的艺术总监希利尔先生对林绍灵的画很感兴趣,做了大量的前期宣传。开幕当天,画就被订出两幅。之后,他去了意大利,按常规展览10天左右画要撤掉,林绍灵也准备撤回画作。希尔利先生有些不解,找到林绍灵询问。他急中生智辩解道:“我想画些法国和意大利的风景来替代,或许你们更喜欢。”希尔利说:“我们喜欢的就是你画的中国江南水乡,有特色,再加上你的技法是法国人所没有的。你不介意的话,我们签订一份长期展览合同。”就这样,江南水乡系列画第一次到欧洲展出,一展就达1年之久。
阿基坦大区法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瀚文撰文称:如果说东方印象在西方民众的头脑中还是极其神秘和模糊的话,那么林绍灵先生则为这种神秘又添加了一笔绝妙的注解,这种江南的美景似乎只有天上有,林将对自己的家乡——江南的深爱,用回忆或记忆的方式,将小船流水人家在画面上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些画面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又似乎近在我们眼前,在这些画面中,润泽,惊艳和蹉跎相生。
林绍灵笔下的“江南”,不是花花绿绿,不是一味的水墨氤氲,而是从那些老房子里仿佛看到操劳的大妈,听到朗朗的书声,体味到历史的纵深感。他的画富有意境,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在水彩画发源地的欧洲,受到尊重,这是他多年探索后所达到的境界。
一个没有院校经历,更没有师徒传承的“来自地方的画家”,以自己的成就和影响,令美术界刮目相看。他连续担任五年一次的第九、十、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浙江作品评选委员会评委,作品选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美术“正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多次被中国美术馆与亚洲水彩艺术博物馆收藏,此外,他还担任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水彩》特约编辑。
在林绍灵看来,光阴中逝去的是风景,而他找回的却是艺术。
